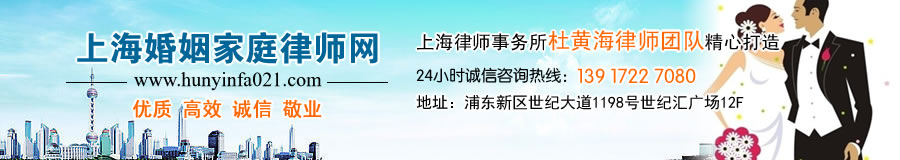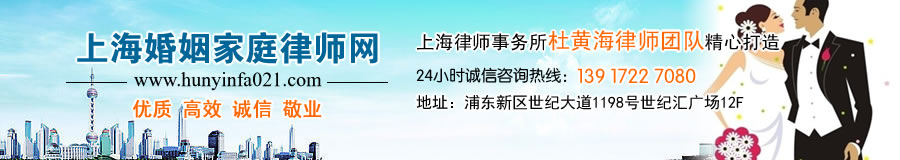我国《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改旧公司法语焉不详之弊,从立法角度对实务中“继承人只能继承股权的财产价值,不能继承股东资格”的做法做出纠正。也从立法上提醒创业者关注自己的身后之事,关注其他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公司人合性的维持,使其注意事先做出针对性的安排。股东资格继承是一个跨部门法的交叉性问题,所以应该结合继承法乃至物权法等民法相关部门法,综合对比考查,以进一步从理论上解释并明晰之。
一、股权继承的性质
股权继承属于股权变动的一种形态,但与股权转让不同,股权继承属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股权变动。我国《继承法》第2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法定继承的情形下被继承人的死亡就使得继承人取得继承股权的权利,被继承人的死亡属于与继承人的意志无关的事件,所以此时属于基于事件引起的股权变动。在遗嘱继承的情形下,则必须有立遗嘱的单方民事行为和立遗嘱人死亡的事件这两个法律事实才能够发生,所以此时属于基于单方民事行为和事件这一事实构成引发的股权变动。
应该指出,从解释论上看《公司法》第76条存在一项立法漏洞,它没有说明因遗赠引发的股权变动问题。而我国《物权法》第29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参照该规定,我国《公司法》第76条明显地涵盖案型过于狭窄,应该对其进行目的性扩张,以实现该条之立法意旨。相应地,从立法论的角度未来《公司法》第76条前段应该修正为:“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可以取得股东资格。”当然在遗赠的情形下,受遗赠人若想取得遗赠人的遗产尚须根据《继承法》第25条第2款及时做出接受遗赠的意思通知,所以此时股权变动的原因则属于遗赠人死亡这一事件、遗赠人遗赠这一单方民事行为和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这一准民事行为组成的事实构成。
以上属于根据引发股权变动的民事法律事实是否与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的意志有关而做的分类。从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股权取得的前提条件看,不单单是建立在上述民事法律事实的发生上,还依赖前权利者的权利,也就是说其股权的取得是基于前权利者的权利产生的,他必须对前权利者的权利进行证明。具体地说,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必须证明作为源泉证据的出资证明书或者股票等证权证券的存在,并可据此根据《公司法》第33条或者140条要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或者变更登记。基于此项证明负担的存在,股权继承又属于继受取得。
二、股权继承的客体
从《公司法》第76条表述的文义看,股权继承的客体是“股东资格”。此种规定虽然如前所述终结了实务中的不必要争议,但是却由此引发了巨大的理论争议,集中在:“股东资格到底能否继承”,及“继承的到底是股权还是股东资格”。
《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我国《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也规定:“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对此有学者主张应该将“股东资格”的说法修改为“出资证明书或者股票等有价证券”,这样就可以与《继承法》很好地配合。
“股东资格” 的说法确实与《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不协调,其本身也非规范法律术语。但是将继承的客体改定为“出资证明书或者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做法也不彻底,因为所谓的这些有价证券在公司法上对应的出资证明书或者股票本身属于证权证券,它们只不过是一定股权或者股份这一内容的表现形式而已。
因此结合上文,我认为直接表述为“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可以取得股权”即可。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5条、《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4条、《日本有限公司法》第19条均采此说法。
我国《公司法》为纠正实务中的不当做法而采用了“股东资格”的说法,这明显地属于立法语言表达上的选择错误。所谓的股东资格对应的不过是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共益权而已,根据我国学界通说“自益权和共益权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股东所享有的完整股权。”可见继承客体采用“股权”的表述就可以根除一切不必要的误会。
需要申明的是,股权继承的客体是股权,对被继承人生前在公司中所担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则不能继承,以经理为例(《公司法》第47条、第114条规定须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因为这种职务本身具有纯身份权的属性,且其产生需要经过特定的程序,况且继承人尚且有可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
总之,股权继承的客体限于股权,一切有身份权属性的高管职务等都不能继承。而正如拉伦茨先生所说:“不能继承的权利随着权利人的死亡而消失。”
三、我国《公司法》第76条的规范性质
《公司法》在第五章第二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部分,没有像同法第100条、109条第2、3款、114条第2款、第118条第5款、第119条那样采用“……的规定,适用于……”的引用性法条的立法技术,也就是说《公司法》第76条不属于被引用的法条,《公司法》没有规定其可以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中。那么是否股份公司的股份就可以当然继承,而不允许像《公司法》第76条那样可以由“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呢?我认为,如果说有限公司股份继承限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具有人合性,那么基于“相同情况,相同处理”的法理,在具有人合性的非上市封闭型股份公司的记名股票继承中也应当允许章程设置限制性条款。所以《公司法》该章节也存在立法上的缺漏,应该区分股份公司的不同类型,不同对待之,增设“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记名股东股权继承可以由公司章程做出限制”的完全法条或者采用准用《公司法》第76条的立法技术。
单就《公司法》第76条的表述形式来看,似乎属于补充性任意性规范,只有在公司章程没有除外规定的情形下,才发挥替代性安排的职能。实际上,所谓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是对股权继承做必要的限制,允许采取类似《公司法》第72条第2款那样的限制性规定,主要“包括授权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以公允的价格收购被继承人的股权。”但是公司章程限制性措施的采用并非毫无边界,不能将第76条但书理解为章程“可以否定对已死亡自然人股东的股东权利的任何继承”。考虑到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章程可以规定不允许继承人继承与股东人身相结合的权利。但是,不能否定股东的合法继承人继承财产性权利的资格。因为对合法继承人继承财产性权利的这样一种章程剥夺,是违反继承法关于继承原则的强制性法律规范的。”因此股权中的以财产性内容为主的“股东投资本来目的所在”的自益权是绝对不容限制剥夺的,否则就相当于剥夺死亡自然人股东的股东权益。从长远来看也会妨碍股东投资的积极性,妨害社会公共利益。
可见《公司法》第76条的但书规定使得本条具有混合性规范的特点, 即当公司章程对股东共益权限制时,章程中的限制性条款优先适用,此时该条前半句属于补充性任意性规范;当公司章程对股东自益权进行限制时,章程中的限制条款无效,此时该条前半句应属于强制性规范。我觉得实际上此种混合性规范在解释论上还可以采用目的性限缩的方法来处理,即将该条归为补充性任意性规范,但是将章程限制性条款的范围限缩为对股东共益权的限制上。这一点也适用于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记名股东股权继承的章程限制问题上。
综上所述,《公司法》第76条的抽象概括性和立法技术上的众多缺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解释论上的难题,通过上文分析,在立法论上对该条提出的完善建议是将其修改为:“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可以取得股权;但公司章程对股东共益权另有规定的除外。”基于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的法理,应当在《公司法》在第五章第二节增加“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记名股股东共益权继承可以由公司章程做出限制”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