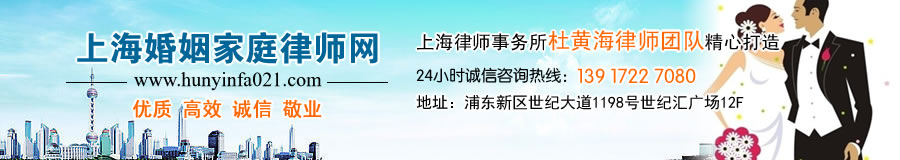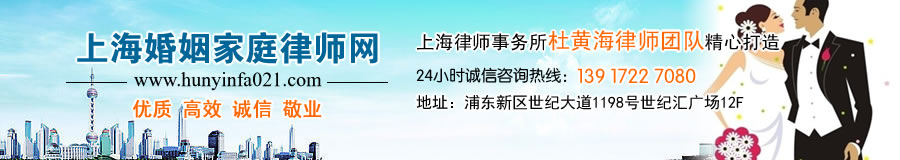【简要提示】性工作者所育子女的亲子关系确认纠纷具有特殊性,为防范摸索证明问题,法院应严格适用亲子关系推定规则,结合证明责任与职权探知主义,审慎认定间接事实,对一方违反诉讼协力义务的行为依据实施目的、程度、效果等进行综合评判,通过减轻或转换证明责任以实现当事人利益的平衡,充分保障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及合法权益。
一、基本案情
原告:赵某甲
被告:施某某
被告施某某系本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沿路1028弄2支弄39号1102室产权人,并曾于2014年起至本市浦东新区一会所消费,此后包括2015年7月间多次与自称“王某”的女性工作人员发生性关系。2016年4月16日,赵某乙生育一女即原告赵某甲,其《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栏登记为“孟某某”,出生孕周为40+2周。后经鉴定,排除孟某某为原告的生物学父亲。2016年5月,被告以遭人骚扰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反映与之发生关系的“王某”自称哈尔滨人,26岁左右,在“王某”告知怀孕后,被告删除了“王某”的电话号码。2016年4月2日,被告接到来自18121188888的电话及短信,内容是要解决“王某”孩子的事情,4月中旬还收到陌生号码发的短信,自称小王母亲,此外还遭到来自15134622529的电话骚扰。5月7日,一对上了年纪的男女到被告居住处门外跟被告儿子说通过“王某”介绍要与被告谈生意,被告认为对方系以生孩子为由骚扰,目的为了钱。此后,公安机关根据被告提供的上述电话号码联系到赵某乙及其母亲。2016年6月24日,赵某乙到康桥派出所后告知真实身份并接受了询问,表示其1982年出生,黑龙江人,在博地会所提供按摩服务并化名“王某”,其与被告在会所相识后保持联系,二人多次在会所内发生关系,被告去会所前会提前联系,其与被告接触的一年多时间内也接待其他客人,但2015年7月左右仅与被告发生2次左右的性关系,没有与其他异性发生关系,其发现怀孕后告知被告,但被告此后不再联系;其生育原告后,其母亲与朋友孟某某找到被告居住处,被告避而不见。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其与被告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鉴定,被告予以拒绝。本院多次以发送传票、短信、致电等方式要求被告本人到庭陈述并释明相应法律后果,被告却始终未露面。
原告赵某甲诉称,其母亲赵某乙原在位于本市浦东新区龙阳路1245号博地桑拿会所上班。2014年5月,被告到该会所消费时与赵某乙相识,此后每隔两三天就会到会所与赵某乙见面并发生关系,其间一直保持电话联系,被告有时将钱款支付给会所,有时则直接付款给赵某乙,赵某乙吃避孕药避孕。2015年7月,赵某乙怀孕。同年8月底,赵某乙打电话告知被告怀孕,同时辞职离开会所,怀孕三个月时联系被告欲让被告陪同打胎,但被告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因孕检时发现今后有不孕不育可能,赵某乙无奈于2016年4月16日生下原告,并请朋友孟某某在《出生医学证明》父亲一栏中签名。2016年5月,孟某与赵某乙母亲找到被告居住地,被告不愿露面并报警。此后,赵某乙被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询问,民警告知对方原同意做亲子鉴定但此后反悔。赵某乙现从事化妆品推销工作,月收入四五千元。原告出生后随赵某乙居住在上海,每月开销四千余元,原告认为,赵某乙当时在会所工作时化名“王某”,被告承认与会所中化名为“王某”的女子发生过性关系,而“王某”就是原告母亲赵某乙。被告不到庭又拒绝做亲子鉴定,在此情况下应确定被告为原告生父,并应按2,000元/月标准一次性支付原告成年前的抚养费43.2万元。
被告施某某辩称,2014年6、7月,其前往浦东博地桑拿会所,由一名自称“王某”的女性为其提供了性服务,之后又陆续去过会所几次(包括2015年7月间),与“王某”发生过关系,每次被告向会所支付钱款。被告有“王某”的电话号码,去会所前会提前联系,但并无私人关系。2016年5月,因有人上门骚扰,被告报案并在派出所做了笔录,笔录中被告否认其与“王某”的孩子存在亲子关系,认为是有人利用此事要钱。审理中,被告拒绝到庭陈述及辨认赵某乙与“王某”是否是同一人,同时认为其与“王某”均在服务场所内发生关系并采取避孕措施,且被告六十多岁,已退休,无生育子女可能,也无抚养能力。而“王某”需接待不同客人,故不确认原、被告间存在亲子关系,也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
二、法院的认定和判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某”是否为原告母亲赵某乙以及能否推定被告为原告生父这两个问题上。就争议焦点一而言,公安机关根据被告报案时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到“王某”并了解到了“王某”的真实身份,且赵某乙与被告在接受询问时就双方交涉过程、“王某”的年龄、籍贯、特征、职业及二人接触、失联等内容的陈述并无显著差异。在此情形下,被告虽提出无法确认赵某乙即“王某”,却未提供反证,亦不到庭辨认,故本院确认赵某乙系与被告发生过性关系的会所服务人员“王某”。就争议焦点二而言,法律规定,一方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对此,本案原告出生证上虽记载父亲为孟某,但已由鉴定否定了二人间的亲子关系。被告虽提出“王某”为会所服务人员,但确认乃至推定亲子关系应以男女双方发生过两性关系为前提,而非以同居或长期、稳定、排他的性行为为必要。根据查明情况及被告自认,被告自2014年起,包括2015年7月均与“王某”发生过性关系,该时间与原告出生日期、出生孕周等信息基本吻合。至于被告提及的自身年龄、“王某”职业特点及避孕措施等情形均无法有效排除被告系原告生父的可能。事实上,明确亲子关系不仅关乎身份关系的稳定及家庭和睦,更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出现悬而未决的情况,势必扰乱家庭乃至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赵某乙对原告陷入身份不明的境地难辞其咎,但不正当性行为系男女双方共同所造成。在原告已穷尽举证手段的情形下,被告配合进行亲子鉴定显然成为本案中查明原告身份的唯一有效途径。现被告拒绝做亲子鉴定,已然满足推定亲子关系成立的法定条件,理应确认被告系原告生父。根据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赵某甲年幼,出生后均由赵某乙抚养照料,在此情况下,被告作为赵某甲生父,理应支付子女抚养费。被告虽抗辩缺乏抚养能力,但并无证据印证。本院综合原告的实际需要、居住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及父母的负担能力等因素酌定被告按月支付抚养费8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判决确认原告赵某甲与被告施某某间存在亲子关系,被告施某某支付赵某甲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间的抚养费12,000元,并自2017年7月起按月支付赵某甲抚养费800元,至赵某甲18周岁止。此后,原、被告均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9月1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三、对本案的研究及解析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虽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的推定规则已经对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证明责任进行了说明,但并不意味着相关诉讼的处理结果单纯取决于被告的鉴定配合意愿。事实上,法院对要件事实的探查、认定及对当事人诉讼参与程度的指引、规制至关重要。
(一)原告对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
通常,原告对父子女间存在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应提供初步证据,在缺乏鉴定结论支撑的情况下,这些初步证据往往指向各种间接事实。所谓间接事实是指在借助于经验法则的作用在推断要件事实过程中有所助益的事实,实际上即为与要件事实相关联,具有重要意义之周边事实。[①]典型的间接事实主要包含:生母与被告间发生过性关系,被告具有如生父般对待子女的表现,父子女间外貌等遗传特征吻合,父子女间血型不违背等等。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运用间接事实群组成证据锁链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间接反证”的挑战。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类“不贞抗辩”,也就是以生母于受胎期间与他人有性交行为(“多数同衾者之抗辩”)或者生活放荡(“恶评之抗辩”)作为排除适用亲子诉讼规定的理由。[②]其主要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止生母随意指认他人,造成有失公允的局面。虽然随着社会科技发展及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一设置已被废除,但时至今日仍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女性不贞行为的看法。尤其,本案原告生母从事色情业服务,社会舆论对此类人员难免存在歧视或偏见,但就民事诉讼原则而言,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不能仅以其职业背景而一概否定要件事实的证明力,亦不能武断认为失足妇女提起的诉讼均为摸索证明所服务,否则必将造成该群体人员所育子女的合法权益无法得以有效保障。因此,在被告运用类似不贞抗辩事由进行反驳时,若起到动摇法官对主要事实难以形成确信的效果,则更应充分、谨慎地审核相关要件事实。
本案中原告提供的间接事实包括:原告生母与被告发生过性关系,原告生母与被告的性关系较为稳定,原告出生时间与双方发生关系时间吻合,原告生母与他人的性关系未发生在原告受胎期间,被告对知晓原告生母怀孕后的安抚、失联、回避等态度转变。对此,被告虽未正面回应,但均未直接否认,相反被告认可了两个相当关键的间接事实,即一是双方存在较为稳定、排他的两性关系阶段,二是原告受胎期间被告确与原告生母发生过性关系。由此,依据一般社会经验法则可以看出,原告提出的初步证据已满足推定亲子关系成立的基本条件,而被告关于缺乏生育能力、采取避孕措施、原告生母卖淫的抗辩意见均不足以推翻相关事实认定。
(二)法院职权探知主义的合理运用
在强调辩论主义的诉讼程序中,法院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与各方当事人的距离大致相当。当然,为了实现有区别的公正对待,法律对涉身份关系、社会公益等较为重大问题的处理进行了调整。如涉身份关系时,当事人的自认行为受到限制,而当事人调查意识的欠缺也可能得到依职权调查的补救。就性服务者所育子女的身份确认工作而言,法院非但不能拒绝裁判,反而须尽己所能调查证据,以确保当事人不会因未提出主张或证据即遭受诉讼上的不利益。
本案中,针对原告生母与“王某”是否同一人的争议焦点方面,原告方表示由于该行业的特殊性及人员流动性大,无法提供服务场所或相关同事的证明材料。鉴于上述因素客观存在,原告自身亦受举证能力的局限,本院至双方指认的会所所在地进行现场了解,但被酒店方告知该会所已停止经营,此后核实中又以外包租赁、无联系方式等为由使得调查无法继续。与此同时,原告曾提及在公安机关出面协调阶段被告答应鉴定但此后反悔。对此细节,法院又向公安机关深入了解双方有无直接交涉或提出处理方案。经核实,承办民警反馈被告到所报称有一对50多岁男女上门以中间人“王某”介绍谈生意为由骚扰其正常生活。民警遂根据原告报案笔录以及提供的对方联系方式联系到一名自称“王某”的女子,并告知该女子到所反映情况。该女子次月到派出所后反映真实身份为赵某乙,并承认其母亲等人至被告住处找被告。此后赵某乙再次到所求助,希望民警联系被告出面,但经民警联系,被告予以拒绝。分析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虽然无法直接得出被告曾在公安机关与原告生母见面、确认原告母女身份或协商孩子抚养问题,但至少可以看出公安机关是根据被告提供的电话号码才联系到“王某”并了解到了“王某”的真实身份,而赵某乙与被告在接受询问时就双方交涉过程、“王某”的年龄、籍贯、特征、职业及二人接触、失联等内容的陈述并无显著差异。由此,法院通过各种调查核实渠道,寻找到了确认原告生母身份的突破口,发挥了职权探知主义的积极作用。
(三)证明妨害行为的必要规制
本案中与原告举证、法院积极调查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被告自始至终的不作为态度。这当然也是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中最为常见的一类证明妨害行为。从狭义上来说,证明妨害行为是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出于主观故意或过失,以作为或不作为方式妨害对方当事人利用证据,使其陷于证明困境或不能。为确保公平,法院课以妨碍方一定的诉讼不利益从而加以规制。
本案中,被告除拒绝配合亲子鉴定外,还存在拒不到庭、拒不辨认等行为。事实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但正如司法实践中禁止强制亲子鉴定一样,被告拒不到庭的行为即便通过拘传进行处理,但拒绝陈述、表态仍是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中的客观障碍。从法理上来说,当事人就事实厘清负有陈述相关(有利或不利)事实,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相关证据资料或忍受勘验的事案解明义务。[③]但对违反上述诉讼协力义务的规制方式却未予明确。主流观点认为,当事人有违上述义务的后果应由法官视个案情况而证明责任减轻直至倒置。个人认为实务中较为可取的做法仍是争取当事人的自愿配合,在欠缺条件的情形下,视当事人妨害行为的过错程度、妨害对象的地位价值、替代证明方式是否存在及相应成本等因素综合考量。
以本案为例,亲子鉴定是确定未成年子女身份关系的最直接有效方式,在一方要求鉴定、另一方拒绝配合的情形下,必然面临未成年人身份权益与争议方人身、隐私利益的冲突处理。在非婚生子女享有平等权益及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保护原则下,被告应当对原告方举证做出明确的回应并提供反证。为取得被告配合,承办人多次以发送传票、电讯、单方谈话、上门核实等方式设法获取被告本人的陈述意见,但被告始终拒绝露面。因此,在举证方已穷尽举证手段的情形下,被告拒绝到庭陈述、辨认、配合鉴定的行为显然使原告身份的查明陷于困境,理应承担妨害证明行为的不利后果,适用亲子关系推定规则成为司法裁判的必然选择。
【主审法官】奚少君 【案例撰写人】奚少君
(作者部门:少年庭)
(责任编辑:唐墨华)